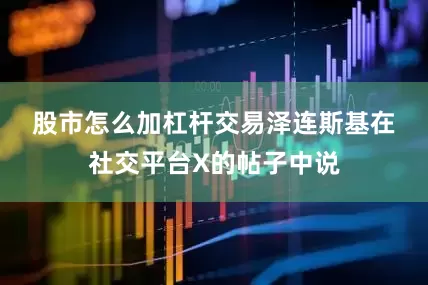1947年,解放军的部队进驻湖北红安县桃花和高桥地区,准备对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。听到解放军即将到来,当地百姓特别是红军的家属们感到十分高兴。
有一天,一位年约六十的老太太走到部队营地门前,询问是否有叫“陈锡廉”或者“谱庆”的人。老太太自称名为雷敏。哨兵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政委后,政委立刻走出营地,亲自迎接她,并搀扶着她说:“您快到司令部来。”
这个老太太究竟是谁,为何会受到政委如此礼遇呢?政委带着她到司令部后,打电话给三纵队的司令员陈锡联,命令他马上赶到司令部。
当陈锡联急匆匆赶到时,他本以为是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,但走进司令部后,他看见几位干部正在和一位老太太亲切交谈。这时,老太太抬头,看到站在一旁的陈锡联时,眼睛顿时闪亮起来,激动地说:“是你,你是我的儿子谱庆!” 陈锡联愣住了,随后满脸喜悦,立刻冲上前抱住了老太太,激动地喊了一声“娘”,母子二人紧紧相拥,泪水夺眶而出。
展开剩余81%为什么这对母子会如此激动呢?原因在于,二十年前,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记忆。
一、陈锡联的童年
陈锡联出生于1915年,湖北红安县高桥区徒山彭家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那个年代,农民的日子极为艰难,家中没有土地,只能租种地主的田地,然而分成比例极为苛刻,很多时候种出来的粮食连交给地主的分成都不够,生活困苦。家庭中子女众多,陈锡联家中人多地少,家里压力很大。
当陈锡联三岁时,父亲因病去世,而母亲雷敏怀着另一个孩子,生活变得愈加艰难。为了维持生计,雷敏将大女儿送到地主家去帮工,虽然日子艰苦,但总算能吃上一口饭。之后,雷敏带着陈锡联四处乞讨,但因为她怀孕了,人们见了她们母子总是视若避瘟,连一点施舍都没有。有时经过地主家门口,狗甚至会扑过来咬人。
后来,她终于找到一个地主,勉强做些帮工,但生活依然艰辛。陈锡联常常忍受辱骂和嘲笑,而这些困苦的日子让他心中种下了参军的念头。看到红军正在与日军作战,他认为红军是“好人”,但年幼的他不能自己参军,于是母亲在他脚上绑了一根红绳,以防他偷偷离开。然而,14岁那年,陈锡联在干爷詹才芳的带领下,决定参军。詹才芳起初拒绝,但最终陈锡联如愿以偿,成为了一名红军的勤务兵。
二、离别与革命
陈锡联参军当天没有告别母亲,他偷偷溜出家门,躲在山里一夜。母亲四处寻找他,痛苦不已,但心里更担忧的是,儿子离开后生死未卜。得知儿子参军后,母亲受到了地主的毒打,但她坚信,这才是陈锡联的出路。
从此以后,每当她听说附近有红军经过,就会问:“你们队里有一个叫谱庆的,真名叫陈锡廉吗?”事实上,陈锡联的名字在军中被误写成了“陈锡联”,他自己也不识字,错别字就这样传开了。
陈锡联在军中的表现非常出色,尤其是在战斗中,他勇敢异常,被同袍们称为“小钢炮”。无论是反“三路围攻”,还是其他重大战役中,陈锡联屡立战功,甚至被李先念称为“打仗数第一”。
三、母子久别重逢
1947年,解放军在红安县展开进攻,陈锡联这次也回到了家乡。此时,他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能见到母亲,因为他知道战斗结束后又要继续作战。但没想到,母亲雷敏竟然找到了部队。
当陈锡联听到“谱庆”这个名字时,心中一震,细细一看,面前的老妇人和母亲确实有几分相似,他确认了,这就是他失散二十年的母亲。母子二人激动地紧紧相拥,弟弟也赶来抱住他们,一家人终于团圆。
原来,是弟弟陈锡礼主动担任解放军的向导,他在闲聊时提到:“我哥哥陈锡廉也是解放军,现在是三纵队的司令。”这让解放军的战士们惊讶万分,立即将消息传给了陈锡礼。陈锡礼听到消息后,赶紧回家告诉母亲,雷敏于是决定亲自去司令部找儿子。
这次母子重逢,经历了二十年的思念,二人整整聊了一夜,倾诉心中的痛苦和喜悦。第二天,陈锡联不得不继续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,战争不等人,他不能因个人情感而耽误战斗。
临别时,陈锡联对母亲说:“娘,您放心,胜利就在眼前,等胜利了我就去接您!”母子依依惜别,但天各一方的命运,注定让这段团聚的时光极为短暂。
四、母亲的离世与陈锡联的思念
陈锡联虽然在战后积极工作,成为了二野三兵团司令员,并带领部队参与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等重要战役,但他始终没能将母亲接到城市。母亲坚决拒绝了他搬到重庆的请求,表示自己习惯了老家的生活。
1979年,陈锡联的母亲因病去世,陈锡联没能及时回到家乡,直到1997年李先念纪念馆落成时,他才有机会回到故乡,站在母亲的坟前,满怀思念地诉说着对母亲的感恩与悔恼。
这段母子离别重逢的故事,展示了无数革命先烈为人民的幸福生活做出的牺牲。陈锡联和他的母亲经历的艰辛与痛苦,正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无数家庭的缩影。
发布于:天津市做股票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正规股票配资网站现有产品均处于临床阶段
- 下一篇:没有了